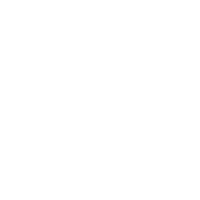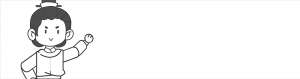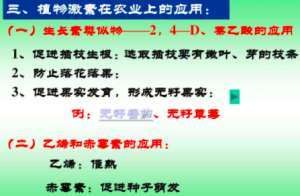哈尔滨种植头发(春动松花江)
时间:2024-03-09 05:29:56
点击:次
来源:黑龙江日报
每年三月中旬,松花江哈尔滨段的冰层开始融化。
如果读者稍有地理常识,就会知道在此之前上游的江冰早已融化。滔滔不绝的松花江水,从稍暖的长白山北麓沿着西南/东北方向的河床向着微寒的松嫩平原昼夜奔涌着。当喧嚣的活水抵达哈尔滨江段的时候,就会遭遇死冰堡垒和低温天气的阻拦,因为松花江哈尔滨江段还没解冻呢。但是随着气温逐渐上升这股不可逆转的大势,这里的松花江也就不得不加入解冻的行列之中。只是解冻并非一蹴而就,需要时间与机会。

松花江开江
开江了,春天来了
其实这时间非常短暂,这机会也是信手拈来。但是不管怎么说,死冰堡垒的防守阵线开始变得并不牢固了,而一波一波的上游活水之冲刷也为死冰的加速融化提供着更多的额外支持。渐渐地,死冰堡垒的防守阵线全面松弛,死冰也渐渐变成了活冰。几乎在一夜之间,曾经刻板而严肃的江冰帝国就瓦解成不计其数彼此独立的诸侯城邦。松花江冰面破碎得如同百衲衣,而冰块浮沉其中则像浓缩的几叶扁舟。如果赶上冰面融化激烈,冰块的诸侯城邦就会发生战争,彼此凶猛撞击,重叠缠斗,发出低沉而雄壮的裂帛之声,由此就会形成气势澎湃的开江景观。当地人称之为“武开江”,反之就是“文开江”。虽然这让不少人兴奋地站在萧瑟的江堤上摄影留念,但是更让人牵肠挂肚的主旋律却只有小约翰·施特劳斯的《春之声圆舞曲》——春天,春天来了。
然而哈尔滨的春天几乎是全世界最短的春天。
这么说也许有些夸张,但是有的时候真的就是这样。短的时候,刚刚结束冬天的春天,仅仅过了一个礼拜(足足七天),就嗖的一声飞进炎热的夏天;而多的时候,春天也不会多到三十一天的。
松花江哈尔滨段的春天期限一般在三月下旬与四月中下旬之间。

松花江牌的冰凌
这里春天的主要特征就是冰雪融化,不像江南的春天,到处开花散叶郁郁葱葱什么的。我把头埋进腿窝里,粗粗回忆,北地的春天也就是融化个冰雪,脱掉个厚厚的棉袄棉裤或者羽绒服什么的。除此以外乏善可陈。如果非要说说这里的春天,如果非要仔细甄别其中的细节,恐怕也就是三个基本要点——早春冰雪融化,仲春地上长草,暮春开些小花,而且还没等春花凋敝,夏天就莽撞地闯进来了。但是人们才不管这么多,哈尔滨人尤其不管这么多。憋了一冬天的人们,内心对自由的需要几近于疯狂,几乎每个人都想长出一副翅膀到处嗷嗷地飞一下。憋坏了。有的时髦姑娘甚至刚脱了羽绒服,就露出大腿,把松花江边的斯大林公园或者中央大街当做秀场,喝酒的喝酒,撒欢的撒欢,追逐着乍暖还寒的春风。不释放一下,怎么对得起松花江解冻的内涵呢?不释放一下,怎么对得起生命这一珍贵的恩赐呢?冬天就是一根弹簧,压到春天的谷底也就反弹了。
“江沿儿”的历史
春天里的人是最快乐的。但是冰雪融化之初,让人烦乱的东西也不少,比如说泥泞。但是它并不是荀红军先生翻译的“轰响的泥泞”,而是力冈先生和吴笛先生翻译的“噗噜噗噜响的泥水”,前者虽然更有气势,更有统治感与美感,但是后者才是事实。而人工修建的江堤由于大多铺着水泥与步道板的缘故,并不存在泥泞问题,尤其是松花江哈尔滨段江南部分的主要江堤,因离市区较近受到市政部门重视,修整完好。当地人把这里称为“江沿儿”(沿字在哈尔滨方言里读作四声)。钱单士厘女士在1903年《癸卯旅行记》里记载:“三局设于江沿附近。江沿者,沿松花江岸,距秦家冈三数里,今市廛集处,俄警察局暂设于此。”对于历史短暂的哈尔滨来说,“江沿儿”的历史算是其中比较长的,而且它的实际长度也比较长,走半天肯定走不完。其中最有名的江堤就是斯大林公园这一段。
这段江堤是中东铁路留下来的,它的整体设计与施工都是园林典范。江边原来雕工精致的栏杆,后被实用水泥和其他材料取代。这让怀旧的人唏嘘感慨。其实这个事儿也没有多旧,还是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末叶到二十一世纪初叶的事情呢。江边的雕塑全都是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的社会风格,哈尔滨人也都熟悉了,并没有违和感,正如防洪纪念塔周边的英雄雕塑,黑头发单眼皮的是哈尔滨人,高鼻梁深眼窝的也是哈尔滨人。而江边那些精美的老房子,每到夜深人静的时候也会对江水讲讲自己听过的老故事,讲讲对面著名的太阳岛吧。

航拍松花江畔
江堤沿途十几公里的风景之美是说不完的,更不必说由于草刚刚长出绿芽儿而带来的喜悦感。当哈尔滨人在社交平台晒这些融雪中的草芽儿的时候,距离上海人晒绿萼梅已经过去一个多月了。还是说说松花江边的树和花吧——这些也许更像春天的正式代表。
花是春天的信使
起初,大多数树木只有树皮刚刚返青,个别树木则长出一点儿青少年色彩的叶子。虽然没有几棵树能长出一片完整的叶子,但是这些足以让人欢喜不已。松花江边的树,近处栽植榆柳,稍远则以杨树居多。杨树先长银白的龅牙,后长褐红的穗子。一条条穗子落在地上,毛毛虫似的,虽然给人些许恶感,但因其沾了早春的光,人们并不讨厌。暮春和初夏的杨花就没有这样的待遇,人们对杨花讨厌得要死,尽管它们在诗里“点点是离人泪”。榆树先是结了青绿的榆钱,一嘟噜一嘟噜的,而后变色发黄,被暖暖的春风一吹,小小的铜钿一样的榆钱就落满松花江面,与水相互搅和着渐行渐远。

夕阳余晖中的松花江
花是春天的信使,这是谁也撼不动的,虽然这种比附从里到外都显得俗气。最开始是黄色的迎春花和连翘,可笑的是人们每到这时候都要争论一下什么是迎春花什么是连翘,好像永远分不清它们谁是谁。园林部门也逗,从没想过在它们前面放一个说明的铭牌。至于杏花、桃红和榆叶梅,更是浓墨重彩遮云蔽日。松花江边,桃红占着优势,但在整个哈尔滨杏花才是真正的大佬。人们晒合影大多以杏花为背景。紫丁香是哈尔滨市花,过去满城都是,根本没杏花的话事权。不少人还记得青年宫当年的紫丁香盛景,现在它们只能出现在记忆之中,而与松花江垂直的兆麟街,过去则以栽植精美的紫丁香景观而闻名,香气之黏稠,思之如在梦中。暴马丁香(白丁香/暴马子)虽然开得晚,但是花期长,它大概是潜入夏天领地的少数花木之一,但是爆裂的哈尔滨之夏能把它当盘菜吗?

解冻的松花江
春天只能留在春天里,虽然随后而来的哈尔滨之夏是最美的季节。那时异常凉爽,松花江边的纳凉闲人比过江鲫鱼还多,唱歌剧的、拉小提琴的、玩滑板的、玩帆船的……无论是九站还是航务局,在生机勃勃的市井百态之中活脱脱地上演着一出出人间喜剧,只是明显少了初春的小心与微喜。端午踏青是哈尔滨人的狂欢节,从深夜到凌晨,成千上万人沿着松花江两岸疾走如风,举着一束束正在散发刺激性香气的艾蒿,好像举着一支支“秉烛夜游”的蜡烛。然而不管松花江的夏天多美,让人想念的却始终是冬春交接的那个瞬间,冰雪消融的那个动人心魄的瞬间。
来源:龙头新闻
本文来自【黑龙江日报】,仅代表作者观点。全国党媒信息公共平台提供信息发布传播服务。
ID:jrtt